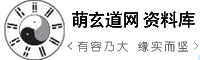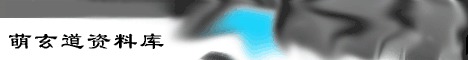老子之“道”与“有”、“无”关系新探———兼论王弼本无论对老子道本论的改造
|
老子的“道”虽然能被体认主体在“虚极静笃”的状态下进行直观的体认,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悬隔于万物之上的孤立存在物,而是内在于万物之中,并表现为万物最基本的运动规律。因此,道本体的体认主体同时也是“道”的运化规律的认知主体。老子将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总规律概括为“反者道之动”。这一命题有两方面的含义: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发展;同时,事物的运动发展总要返回到原来的始基状态(参见陈鼓应,第28页)。对于这两方面而言,“有”、“无”范畴的地位都是极为重要的。首先,就事物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而言,“有”与“无”是老子从纷纭繁复的现象界抽象、提升出来的一对最基本的概念,“有”、“无”之间的相反相成、相互转化集中体现了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法则,本体之“道”就是通过“有”、“无”的相互生成、相互转化而获得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无限生命力。因此,《老子》第二章在列举各种相反相成的现象时,将“有无相生”放在首位。《老子》第十一章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①可见,老子认为“有”和“无”是内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的,是事物基本内涵的两个方面;正是“有”、“无”的对立存在,使事物达到了质料与功能的统一,从而赋予事物以完整的意义。其次,就事物复归于“道”的运动过程而言,“有”、“无”正是连接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万物的必需环节,道本体通过“有”、“无”的分化而产生万物,而现象界的万物也通过“有”、“无”对立面的消解与混同为一而复归于道,所以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因此,对于体道主体来说,对“有”、“无”的把握与提升也是透过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而体察其总体运化规律、进而达到与道合一境界的关键环节,所以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同上)。
其二,与运用主体相关联的“道”。老子体认道本体、把握“道”的运化规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生提供一种终极关怀,为人的生活实践提供价值座标和理论依据。因此,在人生哲学的层面,老子道论的核心问题表现为道本体与其运用者、实践者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老子的人生论主张往往是从其本体论直接推演出来的(参见朱晓鹏,第274页),如老子将无知无欲的“婴儿”状态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是因为道本体的存在方式就是浑沌无象的;主张守柔守弱,是基于道本体“反者道之动”的基本运动规律;主张清静无为,也是基于同样的规律,因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第十九章),只有通过“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的目的。
其三,与言说主体相关联的“道”。由于老子对道本体的体认是通过一种超越了经验与逻辑的直观方式获得的,因此,当他试图对道本体的本质和存在方式进行言说时,就会发现道本体和语言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在他看来,即便赋予先于天地、混沌无名的本体存在一个“道”的称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避免人们对“道”这一“无名之名”的理解有所偏执,老子反复强调“道常无名”,“道隐无名”,道为“无名之朴”。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老子采用的是一种否定的形上学方法:对于“道”这个最高本体,只能说它“不是什么”,却不能肯定它“是什么”(参见朱晓鹏,第95页)冯友兰也曾将这种形上学方法称为“负的方法”(参见冯友兰,1985年,第392-395页)。笔者认为,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否定的形上学方法”或“负的方法”适用且仅适用于对老子“道”的言说方式的概括,而并不是老子“体道”的最根本方式。通过不断的“道不是什么”的否定性规定,固然可以使人无限地接近于“道”,从而获得一种对道本体的近似的、模糊的认识;但这种方法毕竟仍是经验的和逻辑的,它并不能使人直接进入“道”本身;它与老子“虚极静笃”、“涤除玄览”的与“道”玄同为一的直观体道方式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除“无名”之外,老子还用“无形”、“无状”、“无象”、“无为”、“不言”、“不争”、“不仁”、“不德”等大量带有“无”或“不”字的语汇对道本体进行了描述。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命题与后世对老子本体论“道即是无”的概括之间是存在本质差别的。首先,老子上述命题中的“无”字均是作为判断词出现的,仅具有否定义,这些命题的意义在于说明道本体的无规定性和不可直接言说性,老子并没有赋予“无”字以本体义;这与“道即是无”这一命题中“无”字的抽象概念义、本体义有着根本区别。其次,从命题的基本结构来看,老子所提出的都是“A不是B”或“A没有B”的否定式命题;而“道即是无”则是一个“A是B”的肯定式命题,这就把“无”概念化、对象化了。用“道即是无”来概括老子的本体论,毋宁说是后世由于肯定性思维的惯性影响,对老子的否定性论道方式的一种偏离或改造。
综上所述,在剔除了今本《老子》中由于后来衍字而形成的“有生于无”的命题之后,可以发现,“有”与“无”在老子的道论中原本是一对相互平等的概念,它们或是以直接同一性的形态内在于道本体,或是以对立统一的形式存在于“道”的运动规律之中。老子并未赋予“无”以先于“有”或高于“有”的意义,更没有赋予其本体论的意义。
三
在对《老子》文本进行诠释和阐发的过程中,王弼同时肩负着经典诠释与创造性转化的双重使命。而对于作为哲学家的王弼来说,后者显然是更为重要的。他正是通过对《老子》中相关命题的诠释性改造,大大凸显了“无”的意义与地位,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完整的形上学本体意蕴的范畴,从而完成了从老子“道本论”向玄学“本无论”的转化。
在面临《老子》文本中“有无相生”和“有生于无”两个不同的命题时,王弼选择了“有生于无”作为统摄老子有无思想的核心命题。他在《老子》第一章注中即云“凡有皆始于无”(《王弼集校释》,第1页),而对于《老子》第二章“有无相生”的命题,王弼仅说:“此六者(按:指“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名数也。”(同上,第6页)他将“生”字的生成义解释为对待义,这就使“有无相生”成为一个仅仅表述现象界事物正反两方面相对待而存在的形而下的命题。
王弼进而用形名学的方法论证了“有”、“无”与“道”的关系:
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同上,第12页)
王弼将“无”规定为“未形无名”,将“有”等同于“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并且说“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也就是说,“无”是形而上“道”产生有形有名的万物的内在根据。这样,“无”就具有了先于“有”而且抽象程度高于“有”的形上学内涵。
然而,在《老子》文本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毕竟是一个叙述现象界产生过程的、带有宇宙生成论意味的命题。王弼的阐释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还不足以使“无”具有完整的本体论意义。因此,他进而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本体论的改造:“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同上,第110页)“无”不仅是“有”之所“始”,而且是“有”之所“本”,也就是说,“无”不仅是宇宙万有产生的始基,而且是其得以产生的内在本体论依据。对于《老子》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具有宇宙生成论色彩的命题,王弼也对其进行了本体论和概念论的诠释:“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从无之有,数尽乎斯,过此以往,非道之流。”(同上)
他将《老子》原文中的“生”字转换为“由”字,一字之别,含义已大不相同:“生”是产生、生成义,“由”则为根据、依据义(参见康中乾,第172页)。这样,他就把“万物何以产生”这一宇宙生成论问题,转化为“万物如何获得统一性”这一宇宙本体论问题了。他在肯定了“无”是万物获得统一性的内在根据(“由无乃一”)之后,又引入“谓”、“言”的概念,将由一到多的发展过程
|
查看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