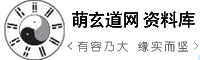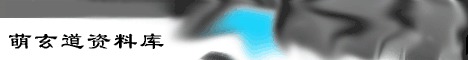诠释与文本的契合——论老子之“道”“无”“有”的关系
| 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句话,我们之所以认同司马光、王安石等人的注解,是因为这种注解为我们准确理解老子无、有的并列关系提供了一种思想支撑。 三、对老子本义的还原:以牟宗三为例 如果说王安石的注解仅仅纠正了王弼注解的偏失,那么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对于王弼注解之阐释可以说还原了老子的本义。牟宗三认为,对于老子所说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应该这样来阐释:“言道以无形无名始万物”即“无名天地之始”,天地是万物之总称,故说“始万物”亦无不可。“道以有形有名成万物”即“有名万物之母”,成者终成也。王弼注解所说的“无形无名”“有形有名”均指道体而言的,如果说“无形无名”是就道体之“无性”来说的,那么“有形有名”就是指道体之“有性”而说的。说道体之“无性”为天地万物之“始”,这是从总体上说天地万物返其“始”以为“本”;说道体之“有性”为天地万物之“母”,这是散开关联着天地万物向前看。简而言之,即以道体之“无性”“始”万物,以道体之“有性”“成”万物。这样,牟宗三从老子思想义理上把“无”“有”看成是并列关系,超越了王弼把老子“无”“有”看作是本末、体用关系的思想误区。 普通只从“无”或“自然”说道,很少注意此经文所说道之“有性”。说到“有”,则从“物”说,“有形有名”亦从“物”说,盖何以能说道为有形有名,因而为“有”乎?如是,“有”只成一对于万物之虚饰词,无独立之实义。但经文及王注确是就道说“有”,此“有”即道之“有性”也。道亦是“无”,亦是“有”,因而亦为始,亦为母。无与有,始与母,俱就道而言也。此是道之双重性。就天地向后返,后返以求本,则说无说始;关联着万物向前看,前看以言个物之成,则说有说母。[5]112 由此出发,牟宗三对王弼“常有欲”“常无欲”断句及其思想义理进行了纠正。虽然牟宗三并没有完全反对王弼的断句读法,但他已然感觉到这种断句方式不能表达出老子的思想旨意,因此他说: 然“常有欲”,实即“常有”也;“常无欲”实即“常无”也(王读虽有据,然此等处却不必拘)。何必著于欲而言之?故不如常无、常有,点句为愈。“常有,欲以观其徼”,徼性即向性,向性即有也。妙用无方之道即在“向性之有”中终成特殊之事物。有而不有,则不滞于有,故不失其浑圆之妙;无而不无,则不沦于无,故不失去终物之徼。如是,则在此“向性之有”中,即可解“有为万物之母”之义。如是,无、有、物为三层,而由道之妙与徼以始成万物之义,更见确切而精密。道亦是无,亦是有,则道之为始为母义,亦可得其确解。此则更得无而不无,有而不有,有无浑圆之玄义。[5]115 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思路,牟宗三对王弼关于老子“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注解进行了重新阐释。我们先看王弼的注解:“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于玄也。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谓之玄者,取于不可得而谓之然也。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则是名则失之远矣。故曰,玄之又玄也。众妙皆从同而出,故曰众妙之门也。”[2]1-2 牟宗三虽然非常肯定王弼的这段注解,称之为“精美”“畅通”。但牟宗三又引申了王弼的注解,王弼仅仅把“两者”界定为“始”与“母”,牟宗三则把“两者”引申到“无”与“有”,最终把“无”与“有”界定为道体的双重属性: “两者”王注指“始”与“母”言,故云:“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谓之始”,道之妙也,即道之“无性”;“谓之母”,道之徼也,即道之“有性”。故“两者”指始与母言,亦即指无与有言,以无为始,以有为母也。后返以求本,则以“无”为始,此即王注所谓“在首则谓之始”;关联着万物向前看以明道之生成万物(使个体存在),则以“有”为母,此即王注所谓“在终则谓之母”。“终”即“要终”之终。徼向个体而终成之也,即实现之也。道有双重性,一曰无,二曰有,无非死无,故由其妙用而显向性之有;有非定有,故向而无向,而复浑化于无。[5]116 四、第40章简本的佐证 对于老子第40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王弼的注解是:“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2]110王弼的注解贯穿了其“以无为本”,“无”与“有”是本末、体用关系的思想主旨,按照这样一种思想逻辑,老子的“无”与“有”只能是一种逻辑上的上下关系或先后关系。 郭店竹简甲本老子《道德经》第40章与王弼本第40章文字上不同,竹简本为“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呈现了道体与“有”“无”两种属性的不同关系,按照王弼本的理解,无与有只能是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或者上下关系,而按照竹简本的文本,我们完全可以把“无”“有”的关系看作是逻辑上的平行关系或者是并列关系。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古老的老子版本,竹简本为我们准确理解老子道体与“无”“有”两种属性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文本的佐证。安徽大学孙以楷先生对这句话的解读颇能切中老子之意旨: “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其中“生于有”、“生于无”之间并不是一种选择关系,如果是选择关系,当作“天下之物,或生于有,或生于无”,“或”字是不可省的。“生于有”与“生于无”是一种并列关系或递进关系,意为:“天下之物生于有,也是生于无”。为什么天下之物既生于有又生于无呢?因为这里的“有”是一般概念,不是指某一具体之“有”,而是指普遍存在,即“有状混成”之“有状”。这个“有状混成”是“混成”,是唯一的无限混沌,是无形无声的,即“寂寥、独立、不改”,也可以称之为“无”。说它是“有”,因为道确实是“有状”;说它同时又是“无”,因为它无形无声无限。“无”是对“有”的规定,这使“有”不落入某一具体之“有”。可见简本《老子》的“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实在是很精彩、很深刻的哲学命题。“有”、“无”是内含丰富而又十分思辨的哲学概念。简本《老子》以有无统一规定了道。后世道家学者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天下之物生于有”又“生于无”,于是重复了一个“有”字,变成了“有生于无”,这样反而把有无统一割裂成无先于有、无中生有,造成了《老子》有无观的内在矛盾,也引发了老子思想研究中的许多争论。[6]154-155 所以,若按照竹简本的“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来说,更能够说明老子并没有把“无”看成是第一性的,把“有”作为第二性的,“如果按更原始可靠的简本理解,‘有’和‘无’并不是相对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而只是同一物种的两种不同表达,即二者都是万物所从出的那个东西。从万物创生来讲,说万物生于‘有’还是生于‘无’,其实是一样的:万物总要有个来处,因此是‘有’;有而不知其名其形,有也是‘无’”[7]116。 五、诠释与文本的契合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无”“有”这样的术语早在老子之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但仅仅是在生活常识领域中使用。老子的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把“无”“有”提升为哲学概念和哲学术语。正像牟宗三所说的,老子所说的“无”“有”指道体的“无性”“有性”,即道体的两种平行的并列的两种属性,这样“无”“有”就成为老子用来说明道体与天地万物关系的桥梁和纽带,这样我们才能够解释老子道体与天地万物的超越与内在的关系:从“无”来谈道体的超越意义,通过“无”来说明道体的本体论意义;从“有”来谈道体的内在于天地万物的意义,通过“有”来说明道体与天地万物的关联性。明代憨山大师对此义理的注解更为明晰: 老子因上说观无观有,恐学人把有无二字看做两边,故释之曰,此两者同。意谓我观无,不是单单观无。以观虚无体中,而含有造化生物之妙。我观有,不是单单观有,以观万物象上,而全是虚无妙道之理。是则有无并观,同是一体,故曰,此两者同。恐人又疑两者既同,如何又立有无之名,故释之曰,出 |
查看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