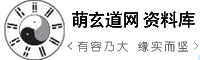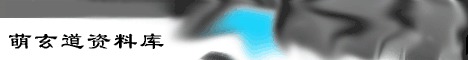《老子》首章与“名”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
|
名为常,则不离其真;不以为为事,则不败其性;不以执为制,则不失其原矣。
也就是说,王弼既承认有一个“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的常名存在,这个“常名”的性质表现为“古今不同,时移俗易,此不变也”。但王弼又说“名”、“称”只是人为之物,在“无物而不由”、“无妙而不出”的“道”、“玄”的领域,则不起作用。从“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不以名为常,则不离其真”来看,王弼还显然反对“常名”的存在,因为“名”和“常”正好相对。勿庸置疑,关于“常名”,王弼这里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我们发现,与上述解释系统不同,古典文献中,对首章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解释系统。例如《文子・道原》有以下的話: 老子曰:夫事生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知时者无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书者言之所生也,言出于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书者也。[5] 这段话行文跳跃,较难理解,但总体上在强调“道”常变易,无常行,虽然作者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和普通人不同,依据“道”无名无形的原理,“事生者”、“知时者”能够认识那些不落于文字、不著于书籍中的、变易无常的“道”和“名”,在行动上采取“应变而动”、“无常之行”的姿态。类似论述又见《文子・上义》: 老子曰: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我们发现这段话的最后几句,也见于《淮南子・氾论》: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两者相比,区别在于两个地方,一是《淮南子・氾论》不见“名可名,非常名”。但有没有,并无实质差异。其次两者都强调先王之书(《诗》、《书》、《礼》、《春秋》)的背后还有“弗能言”(“不能言”)的东西,那就是“常道”,但《文子・上义》整段文意转向讨论变易的问题,转向了圣人的政治姿态,这也是《淮南子・氾论》所没有的。这两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是“言不能言”这种特殊的说法。因为前一个解释系统只说“道”是不可能“言”的,然而,这个系统则大张旗鼓地突出圣人不仅要“得其所以言”,更要“言不能言”。在黄老道家系统中,“言不能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例如《管子》有以下用例: 故必知不言〔之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心术上》)[6] 不言之言,闻于雷鼓。金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心术下》)[7] 马王堆帛书“物则有形”图是一个类似式盘的内圆外方的图案,其中残存有三层文字,其内容是运用道家道物二分理论和心术理论阐释君臣关系。(参见曹峰)其中最外层即方框内侧残存文字为“物则有形,物则有名,物则有言,言则可言”,这应是与臣下相应的形而下的层次。圆圈外侧残存文字有“终日言,不为言。终日不言,不〔为〕无言”,这应是君主应有的姿态,“终日不言,不〔为〕无言”类似《心术上》的“不言之言”、“无形”之言,这样的言要胜过臣下“终日”之言。“终日”之言其实“不为言”,或者说等于“无言”,而“不言”即处于“阴”的、强调“应”的姿态却实质上“不〔为〕无言”[8]。也就是说,“物则有形”图没有完全否定“言”,而是强调更高层次的“言”,强调把握“道”的圣人应当拥有更高的表达方式[9]。 再来看《文子・上礼》: 故先王之法度,有变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文子》的《上义》和《上礼》都强调“道”常变易不居,并由此引出圣人与时而变的政治哲学,《文子・上礼》更明确指出,圣人要“不制于礼乐”、“不制于物”、“不制于法”。 《韩非子・解老》有一段话,只谈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没有言及相应“名之可名,非常名也”,也许当时尚未出现“名之可名,非常名也”也未可知。 凡理者,方圆、短长、麤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与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按照这里对“常”即“不死不衰者”、“无攸易,无定理”、“非在于常所”的定义,可以看出《韩非子・解老》既突出“道”绝对的一面,又突出常变的一面。而绝对和常变是正相统一的。这段话背后有“道”、“理”相对或者道物二分的思想背景存在,“理”和物相应,故而是可“分”、可“定”的,“道”则相反,是“无攸易,无定理”、“非在于常所”的。 河上公章句本对“道可道”的注释为“经术政教之道”。对“非常道”的注释为“非自然长生之道也。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晖。灭迹匿端,不可称道。”对“名可名”的注释为“谓富贵尊荣,高世之名也”。 对“非常名”的注释为“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当如婴儿之未言,鸡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处石间,内虽昭昭,外如愚顽。” 这也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作出的解释,“非常名”不是指“恒常不变的名”,而是说最高的名是无形的、含混的、不确定的、不可为外物把握的。相反,普通的“名”指“富贵尊荣,高世之名”,是“自然常在”的。 因此,这条解释路线,主要不侧重于“道”是否可以用语言表达,用经验感知,而侧重于道之无形、无名、常变不定之一面,侧重将“不言之言”视为更高层次的“言”,按此逻辑推理,我们可以将“不言之言”等同于“非常名”。《文子・上礼》更明确提出“非常道”、“非常名”是圣人应有的姿态,即“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这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河上公本的“非自然常在之名”也隐含有这样的意思。 两条线索的最大区别在于“名”是知识领域可以把握的对象,还是政治领域可以把握的对象。作为前者,即便的确存在与“常道”相应的“常名”,那它也是不可认识的。作为后者,尤其在黄老道家那里,“道”和“名”正是圣人必须把握的对象。可以说今本《老子》二十一章也有此意。 后世的学者对于这样两条线索,多取前者之解说,但也有融汇综合者,如近代学者朱谦之就作了折衷和调和。朱谦之称“道”为变化之总名,说“道”中“有不易者在”。他同意俞正燮的说法,即“老子此二语,‘道’‘名’,与他语‘道’‘名’异。此言‘道’者言词也。‘名’者文字也。”朱谦之作进一步阐释,“《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也。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也。”(朱谦之,第3-4页)也就是说,朱谦之认为“道”是可以用言词说明的,没有永久不变之道。“名”是可以用文字书写的,没有永久不变之名。这样朱谦之把两种解释系统融合在了一起,既说“道”中“有不易者在,此之谓常”, 又说没有永远不变的“道”,论及“道”是否可言的问题(朱谦之认为并非不可言), 这两条解释系统在“常”的理解上完全相反,究竟是“恒常不变”的,还是“变动含混”的,理解的不同导致了解释方向的不同。从语法上看,第一种解释似更合理,而第二种解释则有曲解之嫌。因此第一种解释方法,即“能用一般的语言来说明的平常的、普通的‘道’不是常道(恒常之道、绝对之道)。能用一般的语言来说明的平常的、普通的‘名’不是常名(恒常之名、绝对之名)”能够流行,也是有道理的吧。但第一种系统仍然存在矛盾,那就是无法解释何谓“常名”,既然“道”无形、无名,为什么还需要“常名”存在,这样一个难解的问题。 二 笔者在此并不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