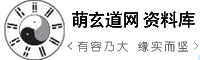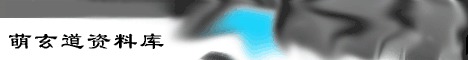| dquo;的学者,占大多数,而把其释之为可“依道奉行”的学者数量不多。大致可区分为以下五种情况(为省篇幅,只列出学者姓名,其注解文字,一律不引):
①把“道可道,非常道”作为一个整体,而判定“道不可言说。”
如战国庄子、韩非子,唐代成玄英,北宋王安石、陈景元、宋徽宗,南宋林希逸.明代释德清,清代魏源,近代梁启超,冯友兰,当代钱钟书,张松如, 任继愈,陈鼓应、冯达甫、卢育三、古棣等。
②认为“道可道”就是“道可以言说”
如唐代唐玄宗、李荣,北宋司马光,清代姚鼐、当代朱谦之、詹剑峰、等。
③对“可道”之“道”的解释,含糊其辞,只强调常道不可言说。
如汉代的河上公,西汉严遵,曹魏王弼,北宋吕惠卿、苏辙,两宋之际的程俱.明代王一清等。从实质上来说,这类学者的观点,不是可归之于①,就是可归之于②。两者必居其一。
④把“可道”释之为“可以认识”,实际与“道可以言说”,与②本质是一回事。
如近代严敏、孙以楷等。
⑤认为“道可道”应释之为“道可以践行”(或“可依道奉行”)。
如南宋李嘉谋、谢图南,元代吴澄,明代明太祖朱元璋、薛蕙、清顺治皇帝,近代沈善增、兰喜并、赵又春等。
(二)从《老子》全篇旨意来看,“可道”之“道”在语法上,只能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但不能解释为说明、表达、说出之义,而应解释成“循道而为”(或“依道而应用”,或“依道奉行”),理由有四:
①,从《老子》的全篇来看,第四章有“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第十四章有“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十五章和六十五章有“古之善为道者,……”、三十章有“以道佐人主者,……”、四十一章有“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六十章有“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七十七章有“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等,都是强调认识道的目的在于应用。这是老子论道的目的,只有把其解释为“循道而为” (或“依道而应用”,或“依道奉行”),才与《老子》全篇的目的一致。
②, 《老子》之中的其他地方,没有以“道”为言的例子,但有把“道”活用为动词的例子,如:
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二十一章),其中的“惟道是从。”与“惟命是从”结构完全相同,而成语“惟命是从”来源于《左传·昭公十二年》“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従,岂其爱鼎?”,可见“惟道是从”的“道”,是名词“道”活用为动词;
⑵“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分别在三十章和五十五章两见,其中的“是谓不道”,既可视之为简单句,也可以视之为复合句:①若视之为简单句,则其中的“道”为名词,在此情况下,“是谓不道”的释义为“这叫做不合乎道”。但这种解释,使得整句逻辑不通(因为“物壮则老”是客观规律,合乎道的);②若视之为复合句(“是谓……”为主句,“不道”为子句),则子句中的“道”为名词活用为动词。于是“是谓不道”的释义为“这(指前文所述的做法)就叫做不按道的规则办事”,全句逻辑立马通顺。
可见“可道”之“道”是把名词“道”活用为动词,是老子遣词造句的文章风格;而把“道”作为言(或说)来行文,不是老子的文章风格。
③若把“可道”之“道”释之为“言(或说)”,则其释义扰乱了下句“名可名,非常名”的作用。(见〖五、“名可名,非常名”只是对《老子》全书声明性的注解〗)
④十四章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可视之为对“可道”的注解。
(三)为什么说,把“可道”之“道”释之为“言(或说)”,大悖老子之旨?
因为把“可道”之“道”释之为“言(或说)”,则无论是怎样解释,“道可道,非常道”,都与《老子》全篇的论点矛盾,剖析如下:
①从庄子开始,直到冯友兰、钱钟书,张松如, 任继愈,陈鼓应、冯达甫、古棣等学者,都认为“道可道,非常道”的释义为“道不可说”。
如果此释成立,则无异于把“道可道,非常道”修改为“道若可道,非常道”方可,改句求释,当然有悖老子原旨。
另,退而言之,就算此释成立,那老子的全书共五千多字组成的文章(谈的都是道),岂不成为胡说八道的东西。也就是说,《老子》全文都是对“道”的论述,这必然与“道不可说”之论是不相容。
②如若按唐朝的玄宗皇帝、李荣,北宋司马光,清代姚鼐、当代朱谦之、詹剑峰等的观点,释“道可道”为“道可以言说”,则“非常道”不好解释。
有人想出解释的办法,称:可以言说的道是局部,而道之常是整体,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故此释与“道可道,非常道”没有矛盾。这是在为此释打圆场,但这个打圆场的做法是很糟糕的,因为它忽略了很多“道”之“常”,也是可说的。例如:“道者万物之奥”、“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都是“道”之“常”,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还没有发现这些话有不对的地方,这些“道”之“常”,不都是可说、可讲的吗?怎么能说这些是“非常道”呢?
可见唐朝的玄宗皇帝、李荣,北宋司马光,清代姚鼐、当代朱谦之、詹剑峰等的观点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这一切表明:把“可道”之“道”解释为“言”、“说”、“讲”,都使得《老子》全篇不能自圆。
③只有采纳南宋李嘉谋、谢图南,元代吴澄,明代明太祖朱元璋、薛蕙、清顺治皇帝,近代沈善增、兰喜并、赵又春等的观点,把“道可道”释之为“道可以践行”(或“可依道奉行”)。才使《老子》全篇在这个问题上,是通顺的。因为依道奉行的内容,只能是人们实施的具体行动,其具体内容的本身,自然是“非常道”了。
(四)沈善增对“道可道”的解释虽然与我相同,但我还是不同意其“先秦时‘道’无‘言说’义项”(沈善增:《还吾老子》,P65)的论点。因为他的解释是强词夺理、牵强附会的,反而显得没有道理。
沈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对郭世铭先生观点的反驳,因为郭先生在《老子究竟说什么》文中称“‘道可道,非常道’中第二个‘道’字是‘说’的意思”,并说释“道”为“说”之义,在先秦时期并不罕见。我虽不同意郭先生的结论,但对其认为释“道”为“说”之义,在先秦时期并不罕见的观点,我必须同意,因为这是事实。
这并不是我发疯,对观点相同者,反说其理由不对;对观点不同者,反说其理由是事实。因为真理不靠表决,也不靠人多势众的声势,只靠实事求是的追求。不可否认,哗众取宠、卖噱头、大肆炒作……等,虽可取得一时的人气,但时间是最好的考验,站不往脚的东西终归站不住脚。所以,不论同意或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朋友,凡是对的,要肯定;凡是不对的,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一些不实的说法,还得要实事求是地给予纠正。
我们就看看沈先生是如何批评郭先生的论点:(以下用楷体表示沈之原文)
先看《郭说》(袁注:指郭世铭先生《老子究竟说什么》中的言论)一书中所举之例:
一、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 “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夫子自道”,作为成语,今人确实用来指一种自我表白的方式。《辞源》:“本为子贡颂扬孔子的话。后多指说别人的缺点,不自觉地道着自已的痛处。”无论“夫子自道”是褒义还是贬义,对“道”是“言说”,似乎没有疑义。其实,从上文“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句看,此“道”若为“言说”义,显然不通。对言说,不存在我“无能”、“能”的问题。要孔子觉得“我无能焉”(不管是否谦辞)的“君子”的“道”,应是种难能的行为,译成白话,当作“引导”或“榜样”。而此“道”与“夫子自道”之“道”同义,否则,引不出子贡这句话。所以,“夫子自道”,不是子贡说孔子已经能做到这三点,也不是子贡说孔子借表扬君子而称道自己,而是子贡说孔子以此标准来自我引导(对自己严格要求)。
我们根据沈先生的这段文字,来剖析沈先生的语法逻辑:(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上文中引用《论语·宪问》的一段话中的二个“道”字,分别称之为前“道”和后“道”。)按照沈先生的语法逻辑,《宪问》这段话,前“道”和后“道”只能同义,(否则,引不出子贡这句话。)即如果不都释之为&ldqu |